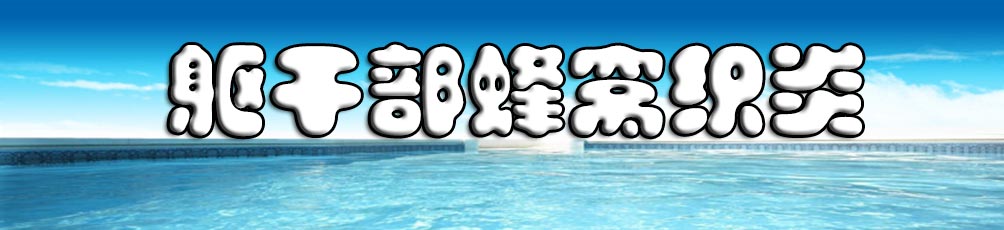
遥远的回乡张远伦
文/张远伦
子弹头论
从军火库里取出它。从一场迷信里取出它。子弹头,你这诗歌的马甲,穿戴着钢和铜。
释放子弹头的过程,就是诗歌写作的过程。因为它长着青铜的样子,火光已经不允许它生锈。每一个子弹头都有一个古代,每一首诗歌都有一个母亲。我们无需探究工业文明和战争传统对每一首诗歌的淬火,但是,闪回和后退一步是必须的。它是有火力的,有热度的存在,在每一个意识和潜意识和无意识闪转腾挪的空间里,它在等待灵感的引燃。在之前,我要忍受那漫长的打磨、装卸、运输和上膛,我极端欣喜地看到扳机朝着历史后退了一下,嗯,毋庸置疑的后退,将诗歌掌控到旋转的势上。这个时候,诗歌形成了运动之前轻微的安静。而我的管道等待它的摩擦已经很久了,这让我管道冰凉的皮肤瞬间获得了沸点。我的管道,不过是让诗歌在规则里通过,这是逼仄而又圆润的通过,是朝着一种轨迹运行之前的热身。当诗歌携带者子弹头冲向空气,一个优美的曲线出现在眼里,来不及审视和纠正,来不及叫它一声:停下来。我们首先感到肩头和胸口被重重地打击了一下。是的,诗歌首先打中了自己,这是后坐力,而我们的身体明显更早感受到了它。这后坐力,是诗歌出现的最根本的力,是诗人自身的温度、力量、速度和结构造成的综合体。这个力,往往是诗人的一趔趄和一震颤来接受的。嗯,诗歌总是打一下别人,也打一下自己。诗歌是七伤拳,子弹头就是掰不开的手指。这样,我们具备了诗歌叙述的语言学基础,你看那飞翔的小东西,还留着彗星的尾巴,那是在告诉我,诗歌独有的美学在于运动。叙述的运动和情绪的运动,以及它将空气推开的圆孔,半径以厘米为单位的小圆孔,本身就是在运动的。这种节奏,称得上是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节奏。在及其短促的时间和及其狭窄的空间里,节奏才能找到,才能具有穿透性。子弹头化妆成诗歌,尖锐地,朝着人体奔来。不幸的人,被称作读者。读者感受到了火药的能量,以及生产工序里的精良,最关键的是感受到了骨头被穿过的疼痛,诗歌的表演就成功了,配得上子弹头这个脸谱和道具。当然,最后通向诞生和死亡、存在和虚无之境的,具有哲学意味的子弹头,更堪从身体里取出来,置于掌心,玩味一番。然后,会想到子弹壳,跌落在诗歌出发的地方,那是一种避免诗歌孤立和线性的怀想,是你和我的联系而非决裂,是自我和他我的呼喊而非折断。
或许,我还在倾听爆炸的声音。不用了,回收吧,只有被诗歌回收的子弹头,才可能让我听到紊乱的脉搏声。不远了,这座即将垮塌的、由血肉虚构的碉堡。
读数论
当我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数字,诗歌便越来越借助数字的排列和转换。世界的中心已经由数字构成,所谓智能化,数字化,其实就是古汉语的象形会意和书写功能逐渐丧失。站在金融中心的每一块砖头上,我都觉得是站在一个个数字上,我的脚趾和手指,都是因为数字而存在的,踩、摁、拨、按,都以数字为基本准则。这时候,诗歌退守血管,进而扼守心门,身体内的数字像是药物一样源源不断。我相信诗歌在变成科学之前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被负数攻破的,每一个负数,都长着一副无辜的猥琐样子。
数字,将亲手送我到诗歌那里去。走在数字的地铁轨道上,断头台一个站一个站地越过,看起来钢化玻璃里的每一个面孔都是向内的,奔向更加智能化的人们,每一个都要做自己的反义词,都要代替光芒去找到黑夜,而黑夜是都是源自遥远天体的空中灾难,一直在预言,从来就在发生。我们或许要经过黑白键,发出简单的乐声,这更加加重的艺术的恐惧。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数字替代。从遥远的五线谱开始,到未来诗歌词汇的匮乏。倾听天籁和阅读古典,都变成少数人的权利。这种权利,都可以用数字来遥控。诗人还在使用隐喻,因为大数字时代只有修辞手法有反抗的可能。
诗歌对数字的敏感基于辨析和规避的本能。我们需要知道二十四重人格是怎么被自我发现的,那将是人对数字反抗无效的自我分崩离析;我们需要知道十一种人生活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,那将是人被数字结构后的样子,当然,庖丁只需要一把刀和一个点,将这个有关骨头的数字纷纷化解。之后,自成体系的数字虚拟世界,那些被无线电和磁场编织的网络,将诗歌带入了静音之中。于是诗歌就成了数字的静音。看上去,这和死亡没什么差别,也和微生物统治地球没什么差别。
如果有人强迫你,让你认识数字“一”,那是你父亲,因为血统和爱;如果我喜欢在诗歌中插入数字,请原谅,那是因为我恐惧。因为,在当下和未来,数学不好的诗人都是可耻的。
流浪论
作为父母的儿子,妻子的老公,女儿的父亲,我是坚决反对诗人被异化成流浪者形象的。但是我坚决捍卫诗人流浪的权利。
人民币排斥异己的方式之一,就是让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诗人,变成流浪者。换成英镑和美元,也是如此。因为意识形态解决不了所有问题,而诗人认为世界是不生长病毒的。只要有战争、压制、歧视和饥渴存在,诗人就更活跃。反抗无果的情况下,人生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最好的逃避办法。因此,诗人流浪者出现了。帕斯说过,资本对诗人们关上钱匣,让诗人变成贱民、幽灵和流浪者。诗人被穷、要穷、乐穷比比皆是,穷不是问题,只要不叫穷叫苦就是了。既要撕裂这个资本社会,又要制造穷困潦倒的泪点,是虚伪诗人所为。
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了诗人,因为诗人与物质世界产生了分裂,难以在理想国里容身。在重建巴比塔的路上,诗人也是无所作为,通天之路永远留给花钱买来砖头的人。这些反讽是诗人的羞愧吗?不。作为人类精神规则最初的制定者,诗人占据着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地位。在《诗经》里,诗人是爱情规则的制定者——情投意合和超越时间空间;在《离骚》里,诗人是国家意识的制定者——至死不让分毫;在古希腊,《荷马史诗》里,诗人是自由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制定者,这几乎就是西方社会现代意识形态之滥觞;在意大利,《神曲》里,诗人制定了真善......从思想意义上讲,这些中外启迪蒙昧的诗篇,都带有宗教般的影响。诗人,作为预言者和释放者,对破坏性和悲剧持有自然的介入观点,介入的特殊形式就是疏离,疏离就是对抗,对抗的特殊形式就是在主流之外流浪。
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很有意思,游,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浪?庄子本质是一个诗人,浪漫主义开先河者,其鲲鹏意象,就是庄子放弃名利,对抗污浊的象征,作为一个官吏,放下身段,变成“游”者,这是一个不妥协的“诗人”,不妥协其实就是内心的流浪。庄子制定的“逍遥”规则,是独立、放达、超自然的规则。“游者”、“隐者”和“流浪者”,都是对抗现实的几类人,本质上是一类人。
这样看起来,诗人被理想国排斥,被人民币排斥,而良知和思想又不是一张大床的情况下,流浪变得合乎情理。好在,他们的双手,没有伸向垃圾箱,没有伸向弱者的头颅。作为一枚鸡蛋,他们不站在鸡蛋一边都不行了,他们要选择的是,在哪一个合适的位置,朝着钢铁,磕破自己。我坚决捍卫诗人流浪的权利,就是捍卫诗人对抗的权利。
诗歌的身体性想象力
想象力是诗歌之热动力。想象力是诗歌之肇始和结束。想象力是诗歌之母。
中国学院传统诗歌向来以挥霍想象力为乐,中国口语立场写作也以在日常化叙述的背后激发读者想象力为己任。如是诗人认为自己离开想象力而写作,那是扯淡。就像诗人如果不承认诗歌本质上的“抒情性”(不管是反抒情还是冷抒情,以及寓言诗和小说体,都会归结到另一种形式的抒情上)也是扯淡一样。
想象力基本上有三个阶段:以最大限度发挥诗人想象力为目的;以最大限度激发读者想象力为目的;以让读者来不及想象为目的。
第一种强调的是诗人才华,运用大量技术性的手段来实现:比喻、拟情、通感、摹状、象征、悖论、倒置、荒诞、寓言等。一般来说,会有支撑性意象以及意象带来的想象空间,借以实现景象(物象)与心象之融合一体。
第二种强调的是诗歌张力,在平常的表述中开掘诗意的深度。这样的诗,往往强调呈现,强调直白,同时在平实的本后实现诗意的转身,诗意的藏,诗意的跳脱延展。这种诗歌,看似藏起了诗人自身的想象力,实则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,让人慢慢品味而不舍。
第三种强调的是诗歌爆发力。常说的捕捉灵感,瞬间、刹那、咯噔一下、怔住了,这类词语可以来表述这种感觉。诗歌往往以表面的断面、截面、极短时间和闭合空间,来展现出诗歌内在的重击、纵深、维度。
想象力往往有自然想象力、人性想象力和神性想象力。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山水画、意象诗,很多都是自然想象力的结晶。当然,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类则是人性想象力的名篇。至于圣经、古兰经、金刚经、道德经和与之相联系的诗歌就具有了神性想象力的高度。于坚认为世界上的冲突本质上是文化的冲突,文化的冲突其实是神与神的冲突。同理,诗歌的高度想象力的区别,实际上是神的想象力的区别。
其实,人性想象力的内涵里,有一种非常具有根本性的想象力:身体性想象力。
诗人的身体性写作往往以自我身体为立足点,在不断自我审视中完成超级自恋和自虐。
诗人,是一个自由愉悦的不及物动词
巴特认为:写,英文towrite,是个不及物动词,不仅是作家幸福的源泉,也是自由的模式。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:诗人,本身就是一个动词。他是自由的,愉悦的,是开启了自我模式的人,是策动自我幸福源流的人。
诗人写下的,是自由,是幸福,是悲悯,是哀伤。诗人最大可能写下的,是墓碑,是遗嘱。虽然不少人热衷于为自己写下虚假的墓志铭,但是,一些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类似文字,还是很值得一读。
“辛波斯卡以精确的讽喻,揭示了人类现实中的历史背景和生态规律。”对于辛波斯卡来说,一生经历了政治现实的三重天,见过太多荒诞,并借助讽喻来写出这个过程中的诗人日常生活。她是一个掌握了严肃性和幽默性的平衡点的诗人,是一个一直在诗歌路途中的一个逗点。她不哗众取宠,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,安于清贫。她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写着的动词,是为自己写下墓碑的动词。辛波斯卡具有巧妙的避免政治核辐射的本领,其原因在于她的隐喻手法。她借助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避开文学之外的介入。我想,除此之外,辛波斯卡纯粹的内心更是她能够坚韧并幽默地面对命运的原因。这样的命运,值得小诗来纪念,值得墓志铭、牛蒡和猫头鹰来簇拥。
诗人这个动词之后,有一个宾语。宾语之前的定语是自由、纯洁和清贫。这个宾语在哪里呢?
诞生和死亡!
诗歌的终端要素
挪威诗人奥拉夫?H?豪格在《诗》极其简练地道出了豪格的基本诗学立场:为农耕写作的隐逸情怀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两个名词和两个动词:铁匠、木匠、理解、取悦。可以说,豪格一生,就是在用心灵理解铁匠,用诗取悦木匠。正因为铁匠反复锻打的铁具、木匠反复铆制的木具,让豪格农夫的诗篇有了精耕细作的可能。这首诗其实说的就是豪格自己,以及与自己产生关联的事物。虽然以《诗》为题,但涉我性很强,是一首用第二人称代替第一人称说出自己一生的诗。
厄尔·迈纳认为文学有五要素:诗人(poet)、作品(work)、文本(text)、诗(poem)、读者(reader),这5种要素必不可少,符号中介是文本,作品是诗人的创作,而诗则是读者所接受的诗,作品、文本、诗有所不同,而两端都是人。就豪格这首《诗》来说,基本上回答了五要素的问题:
诗人(poet)——挪威诗人奥拉夫?H?豪格;
作品(work)——理解铁匠、取悦木匠,写出一首诗;
文本(text)——如果你能写出一首/农夫发现有用的诗,/你应该幸福。/你永不能理解铁匠。/最难以取悦的是木匠;
诗(poem)——我读到并感受到《诗》;
读者(reader)——农夫(含铁匠、木匠)、我、未知。
豪格在这首诗里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要素中,涉及到最本质的终端读者——农夫,他希望农夫发现能有用,这是一个喜欢中国陶渊明的北欧隐士诗人,最基本的人生立场。这个人生立场,就是诗学立场。道法自然,天人合一,这些中国古老朴素的哲学,用来关照豪格,也是有投射作用的。
我们写诗的时候,没有几个诗人会想到这五个要素,但是,当文本完成,进入一定平台并被一定程度接受,那么这五个要素就自动完成。可以这么说:初始要素的诗人本身决定了终端要素读者。你是什么样的诗人,就写什么样的诗,就有什么样的读者。这从逻辑上显示出“为自己写作”的可疑。为谁写、写什么,这是诗人的永恒命题。
否则,诗歌的终端就是白纸、零和坟墓!
“我”主语写作。“我”的饶舌。以及“我”的隐喻
费尔南多?佩索阿的诗歌你会看到太多的“我”。特别是这两首:《英文歌》《我开始明白。我不存在》。简直就是“我的”饶舌,“我”的叠加。这是一个“灵魂分身术”高超的诗人,一个欧洲现代主义的原发性诗人。创作了众多“异名者”,并和“正名者”相互攀越。不管是“正名者”还是“异名者”,其实都是他自己,是“我”。一个终身未娶,孤独难以名状的诗人,一个足不出户的老宅男,除了“我”,能有多少人可写呢?他的世界,就是“我”的世界,就是“我”一个人在场,一个人抱着孤独成双,一个人在词语里建立王国。
这两首诗均来自于他的“异名者”中的“阿尔瓦罗?德?坎波斯”。我以为这是所有“异名者”,和“正名者”中最具艺术性和最真实反映佩索阿内心的一部分。在佩索阿心里,只有三个大师:一个是惠特曼,一个是卡埃罗,一个是坎波斯。后二者是诗人的两个“异名者”。可见佩索阿已经觉得自己是三个大师中的两个了。这种庞大的体系和自我灵魂构建真让人叹为观止。
坎波斯是一个花花公子,双性恋者,一个经历了浪漫主义——未来主义——虚无主义的感觉论者,一个吸毒者,一个捣坏了佩索阿唯一一次爱情的另一个“我”。一个唯感觉论者深陷于乞丐一样的生活中,只能感觉到“我”的荒诞,“我”的虚无,“我”逃遁。
《英文歌》中的我远远地离开了事物,换成灵魂在行走,这种行走,让世界离我远去,与我相关的事物都是无用和模糊的,我甚至灵魂出窍到破裂,随着太阳和星星破裂。在这样的虚无里,我有心脏,是天空和沙漠。诗人把这两个事物合为一体成为一个心脏,一个既辽阔又难以触摸的心脏。我走了,我的灵魂走了,但是还有真实且惬意的一个我,唾液一样,吐在车轮上。
这是一个旅途漂泊者,一个自卑、自厌和对世界怀有敌意,怀有彻骨的绝望的诗人,在饶舌一般歌唱。“唾液”就是真实的“我”,我是肮脏的,但是真实的,击打在世界的车轮上的时候,我有深深的惬意,仿佛我有一种精神的小小胜利。但是,这种惬意,其实是更绝望的懊悔无助。这一个隐喻,像一个刺点,深深地刺中了读者我。我把这种写法,叫做“灵魂透视主义”,作者通过精神分裂般的感觉,用另一只眼睛,反复透视“我”的躯体和灵魂,形成了一种纠缠、迷乱、幻觉般的精神发现。这是旅行者的行走履历,更是旅行者的精神病历。
《我开始明白我自己。我不存在》,亦有译成《《我开始了解我自己。我不存在》的。无论是明白,还是了解,都是“我”对自己解剖的一把手术刀。当我解剖完自己,发现我是不存在的。这种荒诞性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发现,我原来是另一个人,那个人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。同时,我又是和那个人之间的裂缝。我不存在后,成为的另外的影像,是幻化的影像,仿佛在闪动,在逃遁。我甚至成为半个裂缝,因为生活还不容我很顺畅地从裂缝里消失。
然后,我还是呆在屋子里,和巨大的平静呆在一起。最后,我的屋子成为一个假冒的宇宙,这宇宙就是我的所有,就是一个老宅男的所有,就是空虚和孤独的所有。这个宇宙或许就是隐喻我,我本身是一个雷电光的复合体,是物质和非物质的总和,是文学精神和生存状态的交媾,是我和别的我。我就是假冒的宇宙。
况且,佩索阿还认为:“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。”因此这个假冒的宇宙就是我词语体系和存在法则的代名词。
或者说,这个宇宙,就是想象力。
诗歌的真实与真诚
对于一个诗人而言,特别是当代写实主义的诗人而言,他面前的场景和人物都是真实的。但是一旦变成他的诗歌,真实就不存在了。这时候,他需要的是真诚。对于一个对现实世界有极度偷窥癖的诗人而言,利用好诗人的瞳孔,投射一些无限真实的小事物,并通过诗歌将小事物变成无限延伸的心理空间,变成另一种真实,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情。这个时候,诗人的那个小孔,就是摄取诗意的万能机械,安装着镜头、罗盘和撞针。或许,还安装着一个猎豹浏览器,并时常运用其截图功能。请原谅我在这近似于广告语的妄言,因为把诗人比喻成猎豹实在太有意思了。
现实真实不等于诗歌真实。诗歌让现实的真实走向两个方面:减少了的真实和扩大了的真实。现实入诗,必定是现实的减少,不可能复制和对等。同时,诗歌又是扩大了的真实,它会让诗意变得更深远。苏珊.桑塔格《论摄影》里说:“以影像的摄影占有世界,恰恰是重新体验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和遥远性。”诗人是用诗眼来占领自己的世界的,他眼下的真实,会在瞬间变得不真实,变得连自己的思维跑车都追不上。诗歌与摄影一样,截图了生活,却将生活放在水洗后的阳光下,抑或在某些物理性的调整之下(永远不是在美图软件的化妆之下)。这时候,摄影和诗歌,分别从色彩语言和符号语言里挺身而出,成为一个人的独裁。
这样看来,诗人纠结于真实性的丧失和弱化,是没有必要的。活出来的诗歌,重点在活着的内心,而不是活着的躯干上。现实场景截图的诗歌,一味追求逼真是没有必要的。在遥远的柏拉图的思想里,“真”的本意是“真正、源头、原版”,但他认为眼见的真实是最次要最不可信的“真实”。“就柏拉图而言,诗学从未声称过真实......其最客观的真实便是潜在的、抽象的真实,它不同于电磁学、机械学与工程力学等学科,可以用方程式解决实际的问题”(澳大利亚,理查德.哈兰德)。
在诗歌中强调绝对真实是摄影中的资料记录,丧失了艺术在真实之后的拷问和追思。这特别值得底层写作、口语写作以及历史叙事写作的警惕。底层写作中特别注重身体在场和感官接受,而忽略心理在场与真实背后的真相,不少诗人变得比浪漫主义更矫情,比超现实主义更玄幻。一部分口语化诗人用原生的语言来拍摄原生的事物,以为呈现就是最大的诗意,其实这只是拍摄了底片,而要摄影进入装裱程序,最离不开的还是来自天体的光。至于一些叙事性诗歌,特别是有史诗倾向的诗歌,强调历史还原的诗歌,真实性的需要毋庸置疑,但是“诗歌比历史的哲思性和价值要高得多,因为历史求真实,诗歌求真理”(亚里士多德)。诗人对于叙事的意蕴开掘到一定层面,才能成为思想,这一部分思想,其实就是“诗意”。
一度以来,对于生活截片式诗歌的衡量,似乎被量化到“真的吗?”这几个字上。比如读者对诗中某一处的质疑:你这样摹写,是真的吗?她真的那样说的吗?她真的那样做的吗?......是事物本身的真实性让人信服还是诗歌的情怀让人信服,在这里被模糊了,这是明显的对现代主义诗歌假大空、晦涩艰深的矫枉过正,反弹得失去了后拉力。其实,后现代在叛逆现代主义的过程中,自己也有一定程度陷入哗众取宠的矫情之中。诗歌就这样不断否定和叛逆,于是,鸡毛蒜皮写作与崇低写作,又开始被慢慢离弃。当下汉语诗坛,形而上逐渐回归,碎片化被重新剪裁使用,无意义被有意思拉拽。“新诗正在重建汉语的丰裕、中正、朴素、安静,正在走向深厚”(于坚)。这是有道理的。
诗意往往在真实的反面。这有点有悖于逆光摄影的机理。在逆光中,每一个物体都是被天体之光反射后的镜像。而这恰恰是诗歌需要的。至于诗歌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论调早已是昨日黄花,但是生活一定不是诗歌。诗歌确实就藏在真实生活的背阴处,需要诗人通过心理的反射,才能用意识照见而非用眼睛照见。诗歌并非存在于对生活模仿的秩序之中,而是存在于意识的重建秩序中。有的时候,看见的具有诗意的事物,并不等于就是诗歌的诗意,因为真实并不等于是真相抑或是真理。超现实主义者擅于利用真实的反面,以求真实的遥远性。我们在西米克的《石头》里可以看到真实性的延宕之后,是意识的再度追索。他的石头内部并非全部是黑暗,而是有月亮照耀。从而有足够的光辨识那些陌生的文字和星云图。这些陌生的文字是出现在逆光中的诗意,这星云图或许是经过折射和反射后的诗意。这样的诗意具备了丰富性、神秘感、遥远性,进而具有了超越真实的力量。因此说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并非不可调和,从本质上讲,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法,看到了不同的角度。因此也可以说真实的正面和反面不是不可以调和的,我们只不过是调整了光线的运行,而光线的来源都是一个。
这种逆向性带来了诗歌的回眸一笑,真实世界便与美产生了关联。真实本身并不是美,只有当真实带来了另一个领域,美才得以完成。苏珊.桑塔格《论摄影》里有这样的话:“照片即给人以不真实的存在感,又是不存在的象征。”只有当照片带来了人的遐思,同时体现了一种说不出的神奇之处,“似乎照片真的能把人们与另外一个世界联系起来”。我在这里断章取义的意思是为了将诗歌截图式写作的逆向思维、背面思维引入诗意——这另一个世界,这个世界是包含了情怀和思想等潜藏物的。在中国社会强力转型的当下,碎片、截图、剪裁、摄取等现实主义的手段,均可与超现实主义发生关联,这何尝不可?为何不可呢?甚至,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又何尝不可呢?问题在于我们太把形式当成本质,太把所见即所得,太我思故我在了。
在意象主义者那里,他们更多希望通过诗歌超自然存在,而不是依赖于具体洞察力,他们“依据诗性的语言去重构一种新的洞察力”(澳大利亚,理查德.哈兰德)。这样的重构并非对真实的肢解,而是基于真实存在的。庞德认为:劣等的艺术只是不真实的艺术,一种谬误。由此可见,作为欧美深度意象滥觞的“意象主义”,是将真实作为艺术良心的。至于后来的欧美深度意象诗人,各种欧美风情的意象截图,也是来与真实的。他们只不过是将意象推进到诗意的生成器上,而那个生成器,那个“摄影机”,将图片的占比调到弱小,而将图片的反光调到较大。现实主义的截图,也要借助于某一个诗意的“生成器”,那个生成器,更偏重于现场生成,情绪的比重更大。
那么,小场景的呈现,小情绪的宣泄,同样带有文学策略的功用。现实主义在这里并不能完全说服具有哲学野心的诗人。一些混合的、未被表述的、综合性的“意趣”、“意理”,虽然也能在鸡零狗碎中得以一定开掘,但是显然,承载力更大的,是“丰裕的、中和”的写作,甚至于偏执的、艰涩的写作。
至于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抗,也很有意思,罗兰.巴特认为“文学不只是基本的、本质的不真实”,还是“不真实语言下的意识”。如果按照巴特的观点,即使是最真实的“场景再现”和“近复制性写作”,也是诗人在戴着面具走路。理查德.哈兰德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说到:“如果文学不能表现真实的世界,那么也不能表现真实的自然,但至少他可以让我们的谎言变得真实。”那么我们的谎言是什么呢?对诗人来说,就是诗歌。诗歌是另一种谎言,是更高层次的诡计。但,我们需要的是谎言能够让人信服,诡计让人能够臣服。诗歌要让宗教、哲学、艺术通过语言符号进入人的心灵,并与之感应。这样,诗歌符号就成为了另一种真实。事实上,持此观点的很早就有了,那就是亚里士多德,他认为:“说服人的谎言比不能说服人的实话要好。”同理,打动人的诗歌谎言比打不动人的诗歌在场要好。
事实上,这里谈到的截片生活之诗,其实是动态的截片。人们在发明电影之后,就已经很流畅地运用摄影的叙事性了。因此,诗歌原生态叙事是不可避免的。当然,诗人还可以使用蒙太奇和闪回。这是摄影真实中的一种手段真实、技术真实。诗歌中不管哪一种流派,其实终归是手段和技术的区别。文学的本质如人本意识、死亡意识等(如果这也算本质的话),是亘古未变的。
说到底,还是要回到真实与真诚上。当我们对生活进行截图的时候,要做的,不仅是呈现,而且是要再呈现。最后,让人着魔的不是真实,是真诚。诗歌的真诚,包括情绪和情理。因此,别老是幻想着用生活中的抒情来一锤定音,在意和理的发现上,有比移情能力更重要的东西。
比如,在通往消亡的道路上,我们应该摄取哪些镜头,与自我有关联的镜头,并用我们的生命线去串联它们,是需要思考的。当然,我们的小眼睛还不足够关照宇宙,能够摄取多少就算多少吧。
神是人的最高人性
1
这些都是旧日里的旧人物,一个那卡,其实是多个那卡,她和她们。
2
四十不惑,方敬鬼神。把那卡说出来,其实就是把鬼神说出来。看自己,灵魂出窍,一半已枯。我就是那卡的旧日子,那卡是我的旧时光。时间把一切做旧,把我对村庄的想法,染上了更多悲剧的颜色。旧的,是轻的,也是重的。
3
因此这里的那卡,不是一个俗世里确切存在的人物,只是我想象里的一个综合体。我赋予其形象,名字,血肉,情绪和命运。我的残忍,在于将一个美丽的名字带向了雪的温度。
4
这一个系列,叙事多一些,描述多一些,貌似小说,实则是诗。我不管别人承认与否,那卡就是诗歌的,与小说无关。再说,把文体分得泾渭分明,实在是自扰。
5
那卡最初出炉的时候,是与代摆并行的。那卡是美丽和现代,代摆是鳏夫和执拗。代摆能满足我内心对独行侠和匪性的神往,对乡村英雄主义的隐喻;那卡能满足我内心对温暖和未来的追逐,那个神秘、柔软和母性的象征世界令我着迷。
6
阳和阴,乾和坤,神灵与巫傩,就是代摆和那卡。
7
这是行将消失的文化的挽歌,当然,也是企图挽留的一点挣扎。危机感和认同度,将那卡系列诗歌推向文化濒危的形象化叙述中。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,也做不了。
8
神灵的出现,是人的最高人性。因此我在余生会相信这一点。
9
仅仅满足于小格局的人性,是诗歌的矫情。也可以说我矫情。这个世界里,相信神灵的人,太多了,因此艺术中充满虚假,文学中满是伪劣。我们需要把自己先洗干净。
10
这个系列,让我在写作中有了久违的仪式感。
11
法师,是村庄里的请神人;银匠,是村庄里的请神人;诗人绝不是村庄里的请神人。诗人是送神人,负责减少村庄的悲伤,特别是减少心灵的创伤。惟愿所有神灵来到我的村庄,可以什么都不干。
12
好吧,上香!让诗歌里的那卡深受银子的祝福!
野猫说
父亲来电,我家最后的两只公鸡,被坎上人家毒死了。
坎上人家最近常被神出鬼没的野猫骚扰,掠走和咬死好几只鸡。诅咒无效,下毒。那只野猫来源几乎无从考证,坎上人家和我父亲都没见到过这只野猫。村庄的生命力越来越稀薄,坎上人家仅有老夫妻在家,儿孙们都在城镇里挖墙壁扩大生存空间;我家也只有老父亲留守村庄。村庄像一个盛大欢场,草木繁茂,野物自由交媾、生殖和出没。野猫开始了向人类的逆袭。
坎上人家为了对付这只野猫,颇费苦心。先是老人家重新装上了捕兽夹子,试行一晚无果,而又担心自己起夜撒尿踩错地方,取消A计划。然后夫妻俩商量加固鸡舍,围了两层红砖,可野猫竟然从屋顶找了一个破瓦缝隙跃入鸡舍。村庄里的杀手显示出非凡的天赋,B计划破产。迫于无奈,施行歹毒的C计划,夫妻俩在自家鸡舍的屋顶瓦沟子里施下毒药。这时候,坎上人家发现了另一处阻截野猫的场所,我家的鸡舍和鸡舍上的屋顶。他们在一个漫不经心的黄昏,漫不经心地朝我家的屋顶放了几粒毒玉米。恰巧我家的两只公鸡,都飞到了屋顶。它们的扑腾对于宁静的村庄来说就是一场安乐死,要不是掉了两片青瓦,它们的死亡根本就是无声无息。对于老父亲来说,拥有小块土地,就可以漠视全世界,拥有三只鸡,就相当于活出了田园本色。如今,一只寡居的母鸡,带着身体里尚未浑圆的众多蛋仔,蜷缩于庭院,羽毛黯淡,而老父亲脚步漂浮,灵魂显露出锈铁和粗纤维的形状来。
父亲与坎上人家的对话在十分钟内迅速完成。父亲:你家毒猫的药放在哪里的呀?坎上人家男人:都放在高处的,你家屋顶上放了点。父亲:放哪里不好,放我家屋顶?坎上人家女人:我们赔。父亲:把放在我家屋顶的药收干净了,我还有一只老鸡母。坎上人家男人:你家死的公鸡不一定是吃我放的药死的。父亲怒:这么说,我不依,我也去买药来放你家屋顶试试?
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,陷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奇想之中。一个村庄即将消失之前,是否会让野猫、孤豹、独狼等具有豪强禀赋的物种入侵许久。那只神秘野猫,或许是前年被叔父一家抛弃的那只小女猫长大了。如今我多写一些以诸佛村为符号的乡村题材诗歌。设若要我在老人、鸡、野猫之间做出诗歌写作选项,显然是不能的,除此之外,这三者形成的故事性和人性,也不是我诗歌的选项,我的最终选项,将会是那一只尚未出世的神秘的野猫女儿,她有罕见的昂贵的家猫血统,由世代驯化到野性释放,这个过程不被凡俗所见。
赞赏
人赞赏
北京白癜风治好要多少钱河南白癜风医院哪家好